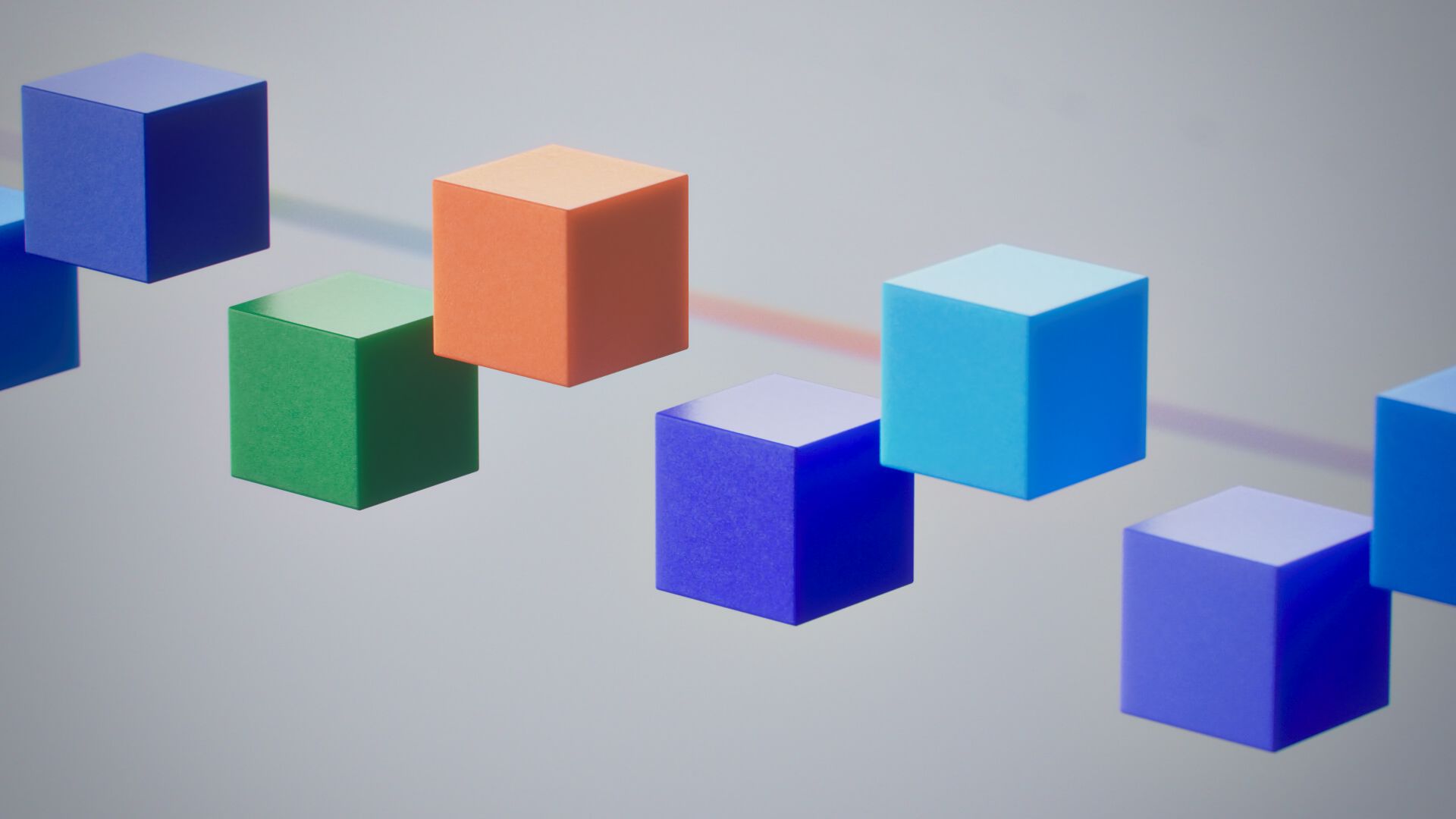初夏的傍晚,太阳已经落下,燥热褪去,西边的天空洇着日光的余烬。我站在房前,看着屋子的影子逐渐与灰土融为一体。门口的白栏杆还是去年夏天朋友来时和我一起上的漆,如今也都干裂开来;风把门廊左侧的秋千椅吹得吱呀作响,我已经有段时间没做枫糖咖啡,谁还记得要去给老旧的轴承添油呢。如果托比还在就好了,晚饭过后我们总在门口玩飞盘,没有沙尘的时候还好,一旦北风呼啸,飞盘大战就会变成我们的洗澡大战。我向屋顶上望去,那块黄色的飞盘还在那,我再无心将它取下来。大熊星座出现在地平线上,它们依旧闪耀,就算这个世界被霓虹笼罩。
现在还不是风滚草肆虐的季节,但我似乎听到了什么,回头望去,除了一片死黑和我的老道奇,什么都没有。我的视力又退化了吗? 可能吧,我不记得上一次去镇上的药局拿维生素A是什么时候了,那天下了大雨? 算了,大雨总是很稀有的,看屋檐管道下的水瓶就知道,我总想着拿这些积攒的雨水浇花,但那些脆弱的生命比托比离开的还快些,我都没来得及记住它们的颜色,花坛只得被拿去当做工具箱。屋里灯关着,门廊的也关着,或许上次刮风时已经坏了。年轻时我有多讨厌家人不开灯,黑暗是年青人的敌人,是恐惧的来源,但我已经忘了为什么恐惧,我敢保证,这方圆一英里内是不会有活人的,大概只有淘金热时留下的骸骨和我作伴。强尼一家搬走时,我送给小强尼的望远镜,他还留着吗? 现在想想,城里的光那么晃眼,连鸟儿都会迷路,望远镜是百无一用的。好吧,没有用也罢,身边的人都走了,托比也走了,我有24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了,现在我应该去看看电视了…
只看着他的背面,像是在咳嗽,接着是一阵呜咽,他僵硬地弯下腰,泪滴在干燥的土上,瞬间就被黑暗吞噬。他再也不会像年少时那样嚎啕大哭,没有力气在暴怒时把手边的东西扔出几米。寂静片刻,他拖着他瘦削的身体上了三级台阶,纱门关了。门廊的灯亮了,灯光黯淡,混着沙土色的阴影,但他晚上总是留着这盏灯,他说他在等待戈多。